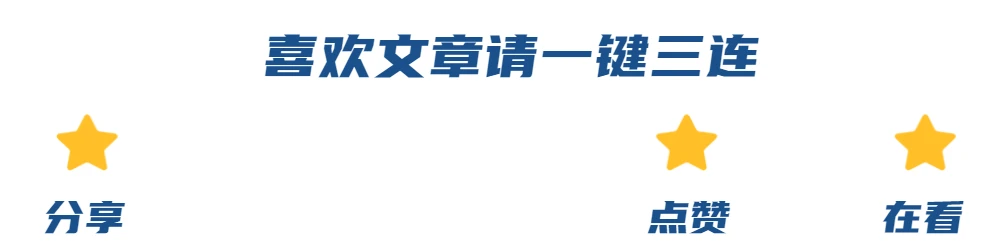阅读预计 19 分钟
“全球百大思想家”潘卡吉·米什拉作品首度引进,读者翘首以盼的出发之作 | 见证重磅级知识分子的顿悟时刻,越接近内心深处,就越理解外部世界 | 一个青年长达十年的寻求自我安顿之旅 | 《纽约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联合推荐
原书名:An End To
Suffering: The Buddha in the World
印度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实现迅猛发展,但在这腾飞的新世界中,大多数印度人找不到自己所属的位置。
在这样一片大陆上,潘卡吉·米什拉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旅程。他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村庄出发,拜访不再辉煌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前往商贸大厦与露天排水沟并存的德里,倾听青年对佛教等古老思想的不满;在暴乱不断的克什米尔,遇见一个个只能在封闭阴冷的房间中泄愤和哭泣的异见者;最后回到喜马拉雅山麓的村舍,在这个充满暴力又困惑丛生的世界中,重新书写佛陀。
沿着佛陀的思想轨迹,米什拉行走在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之间,用思考连接现实和历史,在佛陀教诲中寻找终结苦厄的可能性。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
著名思想家、评论家,1969年生于印度,现居伦敦。
长期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后殖民问题,为《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卫报》等媒体撰写多篇评论,以雄辩的文风和犀利的观点著称,被《经济学人》誉为“萨义德的继承者”,被《外交政策》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2008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
作品获多种奖项,《从帝国废墟中崛起》获莱比锡欧洲理解图书奖和温德姆·坎贝尔奖,《愤怒年代》入围奥威尔奖。《苦厄的终结》是他的首部简体中文版作品。
★“全球百大思想家”潘卡吉·米什拉作品首度引进!
读者翘首以盼的出发之作,见证重磅级知识分子的顿悟时刻作为当今绕不开的思想家与评论家,米什拉以细微且别具一格的方式捕捉西方文明下的东方世界变革,被誉为“萨义德的继承者”。雄辩的文风与犀利的思想更为他赢来“毁灭的预言家、悲观主义者、破坏者”的头衔。《苦厄的终结》是米什拉在简体中文世界的首部作品,写给身陷痛苦与冲突的每个人。
★ 真实版《悉达多》,一个青年长达十年的寻求自我安顿之旅
印度社会在近二十年迎来激烈的新旧交替,但这腾飞的世界没有为所有人预留位置。在这片竞争求存的苦拼之地上,潘卡吉·米什拉饱尝心灵无所归属的虚无漂泊感,开始思考终结苦厄的可能。他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村庄出发,追随佛陀的求索之旅,通过发现佛陀教诲中的生存意义,最终完成个人的顿悟,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提供一种可能性。
★ 当西方的物质遇上东方的心灵,在自由与苦难并存的年代寻找佛陀
从古印度吠陀时代到欧洲启蒙运动,从佛教残留所剩无几的佛陀诞生地,到商贸大厦与露天排水沟并存的德里,米什拉穿行于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之间,用思想与行走连接历史和现实,探索充满贫穷、竞争、暴力的地区,试图回答:佛陀对于今天虚无与焦虑的现代世界有何意义?
★ 奥威尔奖得主安德鲁·布朗推荐:当其他人都在合谋让世界变得更恐怖时,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和发人深省的方案
在现代化这场前所未有的竞赛中,西方国家起跑早且始终领先,并设置了终点线。第三世界国家在上世纪中叶先后取得独立,也加入赛跑,但问题是,上一轮的赢家已经将奖杯领走——米什拉从这一思想原点出发,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下探究佛陀在今天的意义,他的思考冷静又深入,复杂又简单,博学又不乏深刻的人文关怀,得到《纽约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等一流媒体联合推荐。
当其他人都在合谋让世界变得更恐怖时,《苦厄的终结》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和发人深省的方案。
米什拉是清醒和善的作家与文思敏捷的思想家,他将对印度历史的全新解读与对西方经典的透彻剖析交织在一起,将佛陀与苏格拉底联系起来,阐明了佛教教义具有先见之明的现代性。他对佛教的思考眼光独到,文笔优美,影响深远,富有启示。
米什拉的作品将佛陀的故事与佛陀出生地附近的村庄,乃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他坦诚地面对“躁动、执着的自我”,并将从佛陀人生中学习到的经验运用到自己所处的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
米什拉的书沿袭了佛教的传统,既冷静又深入,既复杂又简单,既博学又不乏深刻的人文关怀。
米什拉向我们展示了,他不仅是一位天才的传记作家,还根据佛教文献,构建了一个生动、时而震撼人心、如忙碌的医生那般直率的佛陀形象。
对于严肃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内容丰富且富有挑战性的书,邀请读者去探索佛陀跨越几个世纪、大洲和文化的遗产。
作者以坦诚而不情绪化的方式写作,更像是一名知识分子的仰慕者,而不是一个信徒。他设法收集并整合了大量佛教知识,其中包含的奥秘足以让学者和信徒钻研数个世纪。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对佛教思想的概述,其中不乏充满闪光点的发现。
在讲述佛陀的故事时,米什拉剥去了神话的外衣,描绘生活在那时那地的人的故事,并在其中发现了结束人类苦难的可能方案,令人惊讶的是,这方案依旧适应于现代世界。
书中关于历史,尤其是关于精神生活的历史,使得米什拉的书作为游记与传记的融合,成为一本让人难以抗拒的读物。
多年前首次游览喜马拉雅山后,我在返程中萌生了撰写一部介绍佛陀的历史小说的想法。这样的创作不仅有助于学习印度史,还可增添自身急需的古老智慧。我随后开始搜集各类资料,做笔记,还特意寻访佛教的名胜古迹,记录游历体验。
然而,当我逐渐脱离玛舒波拉的生活后,却总是耽于诸多杂务,让我无法专注写作,著书的计划也变得渺茫,就像欧洲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一样开始带有某种注定徒劳的意味。
直到2001年春天某个温暖的午后,我躺在伦敦一个公园里,心情迷惘,想念家乡,著书的念头又冒了出来。
当时,我刚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返回,本想去异国他乡寻找佛教的遗迹,顺便进一步了解阿富汗的政治现状。但时机不佳,仅仅数月之前,塔利班武装摧毁了阿富汗巴米扬山谷的多座佛像,还破坏了不少珍藏在首都喀布尔博物馆中的印度-希腊式佛像。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大街上,憔悴的阿富汗难民在兜售毒品和枪支,清真寺里的阿訇在怒斥异教徒,但看不到4世纪曾居住于此的无著与世亲的痕迹。只有在塔克特依巴依和塔克西拉荒凉成片的古寺建筑群,我才有机会匆匆领会,当初的古希腊殖民者、佛教信众、各类寺院大学,乃至来自中国和中亚的游人如何云集在此。如今,所有这一切因佛教而起的繁华都已消失,无法挽回,印度次大陆上曾经最为知名的佛教中心彼时的盛况也已无迹可寻。
同样在这些地方,近年来逐渐形成了某种国际化的新型宗教政体。长期以来,在当地的伊斯兰学校中,塔利班成员接受有关《古兰经》的最初步的教导,新一代的年轻人准备参与“圣战”。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他们平静地谈论全世界受压迫的穆斯林如何联合,在阿富汗共同战斗,发誓要消灭超级大国苏联。同时,他们还将借由真主的恩典,一并报复美国和以色列,除非这些国家收敛自己迫害穆斯林的行为。
在阿富汗边境某地,我参加过一次伊斯兰教激进派的国际大会,与会成员近二十万人,大部分来自北非、中东和中亚。与会人的主旨大致相同,现场气氛颇像中古时代的沙漠集市:铺天盖地的各色帐篷杂乱无章地聚集在一起,掀起的浮尘像巨大的蘑菇云,成千上万的人在帐篷里穿梭奔忙,或疾行在比栉的小推车间,或快步于琳琅的小货摊旁,小推车上摆放着鲜榨的甘蔗汁和成堆的蔗渣,还有人兜售印刷精美的乌尔都文或阿拉伯文的《古兰经》,还有奥萨马·本·拉登的各式海报——显然,他才是这场聚会的明星。
据我观察,大会成员中不少都是上了岁数的巴基斯坦农民,后来才得知他们是被雇来的,以印度次大陆特有的方式壮大声威。此外则是年轻人居多,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为主,是白沙瓦以南与阿富汗接壤地带的伊斯兰学校的学生。他们有的是多人挤一辆小轿车或大巴士来的,有的半路搭货运卡车,有的坐三轮车,还有的是赶马车来的。他们举着象征会议主办方的黑白条纹旗,沿着横贯数国的知名大干道,穿过周边单调乏味的平原和泥坯土筑的村落,一路兴奋热闹地来到此地。大会演讲者反复提到这些学生,称他们为塔利班的后备军,随时准备为了崇高的目标献身。
大会开幕的当天,一场凶猛的沙尘暴刮倒了不少帐篷,剩下没倒的也都摇摇欲坠,人们纷纷奔逃而出,身上白色的长袍在风中翻飞,一块块崭新的阿富汗地毯失去了原本明丽的色泽,埋没在灰蒙蒙的大地上,混同沙土。尽管如此,演讲仍在继续,而且声势激昂。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历数漫长的屈辱史——十字军、格拉纳达、伊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等等——进而敦促穆斯林投身到抗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圣战”中去。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想清楚如何回应他们的主张。我知道以圣战之名而行的种种腐败,有领导人利用外国和本国捐献者的慷慨中饱私囊,以少得可怜的报酬雇佣年轻人,将他们送去克什米尔和阿富汗战场,充当殉道的炮灰,这些年轻人的祖先也曾创建最辉煌的世界文明,而如今他们的政府受制于美利坚,或恐惧其钳制,他们失去所有对未来的期待,干脆成为自杀式的炸弹袭击者。
对他们而言曾经可能的另外一种未来已告消亡。在那样的未来,人人穿西装、打领带,在办公室或工厂里谋职,控制生育,养活一个核心家庭,开一辆小轿车,本分地当个纳税人。然而,现实中,连保障这些年轻人接受当代教育的世俗学校都远远不够,提供给受教育者的工作机会也少得可怜。
他们之中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有未来。至于其余人,恐怕只能依靠某种精心设计的手段——诸如上千种“援助”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还有关于不发达国家、经济自由化和民主等议题的高谈阔论——维持进步的幻觉。但他们的国家所营造的现代化幻想,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裹挟下,已经足以将他们从土生土长的村庄里连根拔起,逐出故乡。
这也正是我父亲和他无数的同辈人早年面临的命运,对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从旧社会迈向新世界的迁徙是一场跋涉经年而日益艰辛的旅程。如今,这趟旅程看起来不仅无休无止,而且正裹挟着越来越多的人。成千上万生活浑噩无力的人接受所谓平等公正的许诺,被引入一个他们全然无法理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原本可供他们享用的那部分资源早已紧缺匮乏,这些新来者却还在期盼着开发利用它们,好改善自己的生活,像这世上的一小批中产者那样过上富裕的日子。
至于他们之中那些命运更加不济的人,现代化生活不啻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少数几人登顶之后便盘踞山巅,俯瞰着下方的攀爬者艰难地在悬崖峭壁上尺挪寸移,偶尔丢下一条半条破绳烂索,但更多时候扔出的是巨大的石块。这些占山自居者知道,世上再也没有未知的土地和人民可供征服、控制乃至剥削利用,于是他们就只能去砍伐自家的树木,污染自家的水源,设法统治和压迫自家的国民,尤其是妇女和少数族裔。
有些人失去了他们古老的道德秩序,尤其是基于该秩序的权威而产生的固有人际关系与模式,从而也就失去了这秩序的传统保护,于是他们寄希望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激进主义等权威运动,想要通过参与这类运动,将自己的梦想托付给本·拉登那类煽动者,以规避社会的混乱与衰退。
从那次激进主义者的集会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愤怒的演讲者,还是台下狂热的听众,基本不了解、也不可能深入了解美国。但他们出于恐惧和困惑,硬是武断地造出了某种概念,再将自身的苦难连同社会上所有的邪恶罪行,全部归咎到它身上。
他们带着满脑子的敌对观念,开始梦想实现西方人曾经的革命理想:通过迅猛彻底的社会变革,实现经济、法律、政治、宗教、文化等全方位的社会改造,一切从头开始,白手起家,创建一个纯净纯粹的国家和社会——只要变革,就必定能够保障人类的幸福和美德,但要实现这个“乌托邦”,必须先打倒腐败堕落的对手。这一理想伴随着极具宗教色彩的浪漫主义,那是伊斯兰教特有的浪漫。据说,伊斯兰教自古提供了安全与公正,如今更是掌握着一幅关于理想未来的蓝图。
当某些人从关系密切的小社会中连根拔起,在举家背井离乡的迁徙中试图重振身心,融入更大的集团生活;当一个民族篡改自己的历史,还非要将某种本是私人多元选择的自由信仰变为统一的政治意识;当他们将愤怒对准“美国”和“西方”等假想敌,并以革命为名到处煽动世人造反,其行为只会让人觉得他们想要寻找自身的历史定位,但却陷在无垠的虚空中挣扎求存。
然而,从巴基斯坦回到英国仅数周的那天下午,我在伦敦公园又想起佛陀时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同样充满徒劳无功的挣扎。此前,我在伦敦东区附近住了好几个月,一直在写关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治现状的系列专题。那些悠长的白昼、耀眼的阳光、拥挤的街道和公园,让伦敦没有了一贯的沉肃之气;而我满怀思乡的情绪重如沉疴,也是一种痛苦。
我当时三十多岁,算是写过几篇东西,积攒了些许海外阅历。身为普通人的我起点不高,很难不将这一切视作某种成就。回顾以往,大部分时间我都羞耻于贫寒的出身、知识上的匮乏、没有完全掌握一门外语、没有出众的天赋或才华。
之后我之所以能及时克服这些恐惧,部分原因在于我学会了身处现代社会的某些求生之道,包括习得英语,并且在它浩瀚的文学宝藏中完成自我教育。通过效仿少数社会精英,战胜自身的种种劣势,我已在“西方”找到一席暂时的安身之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初来英国时足令我惊奇的一切——异域面孔、仪态举止、外表着装、居住条件、口音腔调——失去了曾经让我迷失他乡而倍感疏离的魔力。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伦敦,却总也禁不住感叹,能够生活于此简直就是人生奇迹,如此际遇在当年居住在玛舒波拉的我看来完全不可想象。还记得初抵伦敦那天,当我走出希思罗机场大楼,步入明媚的秋阳,触目所及的是一大片平坦沉静的绿地,一条条混凝土铺就的宽大马路贯穿其间,路上的车辆精巧如滑行的玩具。
这一神奇之旅也造就了一个怪异的我。回首来路,我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自己:那个在阿拉哈巴德求学的初生牛犊,涉世未深却一心想要干革命,还想去尼泊尔买一顶钟爱的棒球帽;那个在喜马拉雅山中遁世的青年,一边读《弥兰陀王问经》,一边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一本介绍佛陀生平的书;还有那个自以为是却又胆怯惊疑的杂志撰稿人,曾忙不迭地想要逃避老友海伦,过后又令人厌烦地向她打听美国佛教界的现状。从这一连串焦躁不安、只知攫取的“自我”中,我只看到自己巴不得昭告天下的种种欲望和冲动,却看不到谦卑或恻隐之心的一丝痕迹。
我一度自诩志向不群甚至独特无双,但事实是空有满腹愿望,却无甚可取之处,亦无甚重大的影响。而且,我早已尝过思想与心灵无所归属的漂泊感,一想到最终也只能剩下这种漂泊感,我就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慌,无论我如何博学多闻或见多识广。
每当这时,我就想要重返玛舒波拉——实际上我经常这么想。从前在那里的日子,我其实和村民并不亲近,也不真正了解他们。关于那些日子的记忆非常私人,唯有漫长的夏夜、房顶的落雨、树脂的松香,才能偶尔唤醒它们,使之在迥乎不同的风景中鲜活起来。但是,在我的想象中,玛舒波拉早已是如家一般的归宿,我可以在那里找到熟悉的面孔、亲情友爱和慷慨大度——还有也许只对被连根拔起的人而言必不可少的错觉——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一段稳固长存且清晰连贯的过往。
那正是我那年秋天在玛舒波拉开始进一步看清的问题,也是佛陀为他那个时代遭遇战乱的无助世人指出的问题:人类的心灵是一处欲望丛生、仇恨与谬见肆虐之地,它创造了往昔的荣誉、失败和未来的希望,也创造了让人无限痛苦的可能,然而恰恰是这样的精神世界,才是我们借以完全把握自己人生的机会所在。
人的精神世界是史上一切疯狂现象的发源地,是后果难以预测的观念与行动的模糊混同。但人正是由此才发现,一切观念的构成都何等脆弱而主观,毫无实质,本性皆空。人唯有基于对自我的认识,逐步摆脱看似必要之物的束缚,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这自由不在别处,就在当下,就在此时此地,就在佛陀宣称过往是抽象而未来是虚幻的这一刻。
活在当下,始终保持高度的自觉和慈悲,将之彰显于最细微的行动和思想中—这听上去像是可供人应对自身压力的某种自救之道。然而,不断深化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伦理道德观,正是佛陀大胆独创的方法之一,旨在回应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和心灵危机,即逐渐崩溃的小型社会在丧失旧有道德秩序时面临的危机。佛陀以大量话语和行动表明,当人们被剥夺往日基于信仰和社团生活而享有的慰藉,不得不在一个充满新生诱惑和陌生危险的广阔世界中谋求生存,他们就必然遭受漂泊无依之苦。
人类的这种苦境在波德莱尔、克尔凯郭尔、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同样出现过,他们都曾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激情、痛苦和冷嘲热讽描述它。但佛陀不满足于生动地诉说或哀叹,他不仅剖析人类思想和心灵在遭遇环境剧变时面临的陌生困境,还尝试战胜它。在这个过程中,他颠覆了许多隐含在现代政治和经济活动背后的臆断之见。
尽管个人和社会都只顾侵夺他人,谋求自利,导致彼此冲突日甚,但佛陀指出,无论个体还是社会,皆须相互依存共生。他论证了人类自我的多重易变性,人既有可能为苦所累,也有可能主动作为,消除痛苦。同时,他还以此为据,质疑人类通常赖以产生自我认知的根基,即一个稳固而实在的身份。作为一个敏锐的心理学家,佛陀教导人要以彻底怀疑的态度,审视欲望及其升华之后的高尚表象,即基于历史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诱人概念。他还提供了一整套有益于提升道德、保护心灵的方法,引导人以截然不同的眼光,重新看待和体验世界。
回想当初在玛舒波拉满怀憧憬地想要为佛陀著书立传时,我完全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认识。那时候,佛陀对我而言还只是一个半虚构的神话人物,而我自以为可以在他的世界闲庭信步,享受几年惬意悠游的日子。
我虽然也想改变看法,但那时的我总觉得,严缜精妙、宛若神医的佛陀只属于过去,仅存在于历史之中。直到花费更长时间,储备更充足的知识,也积累更丰富的阅历之后,我才终于意识到,佛陀堪称一位与时俱进的当代人。
如今,我在自己所处的世界中遇见佛陀。就在这个充满暴力又困惑丛生的世界中,我看到了佛教的义理,乃至救赎之道可能为世人创造的未来。正是这种醒悟,让我终于可以提笔,开始书写佛陀。
本期编辑:许丙南 穆祎璠
*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政报·100期 | 印反华立场如何造成造成上合组织内部信任赤字?

▲经报·92期 | 从权威数据看,印度当前相当于中国哪一年?

▲军报·14期 | 印密集推出多款新式武器,掀起国防工业小高潮?
▲重磅 | 同是“发展型国家”,为啥中国经济起飞印度却被甩开?
▲重磅 | 先天有缺陷的印度电力市场,如今又遭遇大劫?
相关推荐: 历史 | 来自莫迪老家的印乳业第一品牌,如何创造乳业奇迹?
本文共2686字阅读预计5分钟作者 | Z.H.编辑 | 许丙南 江怡 飞机餐配的 Amul 黄油(上方中间) 去印度的游客可能不一定买过当地牛奶,但想必不少人见过印度航班上供应的小包装 Amul 黄油。 Amul(Anand Milk Union Limi…